W.G. Sebald 与忧郁的政治:论政治抵抗
W.G. Sebald and the Politics of Melancholy
文章探讨了文集《Silent Catastrophes》如何帮助我们应对帝国衰落和权威主义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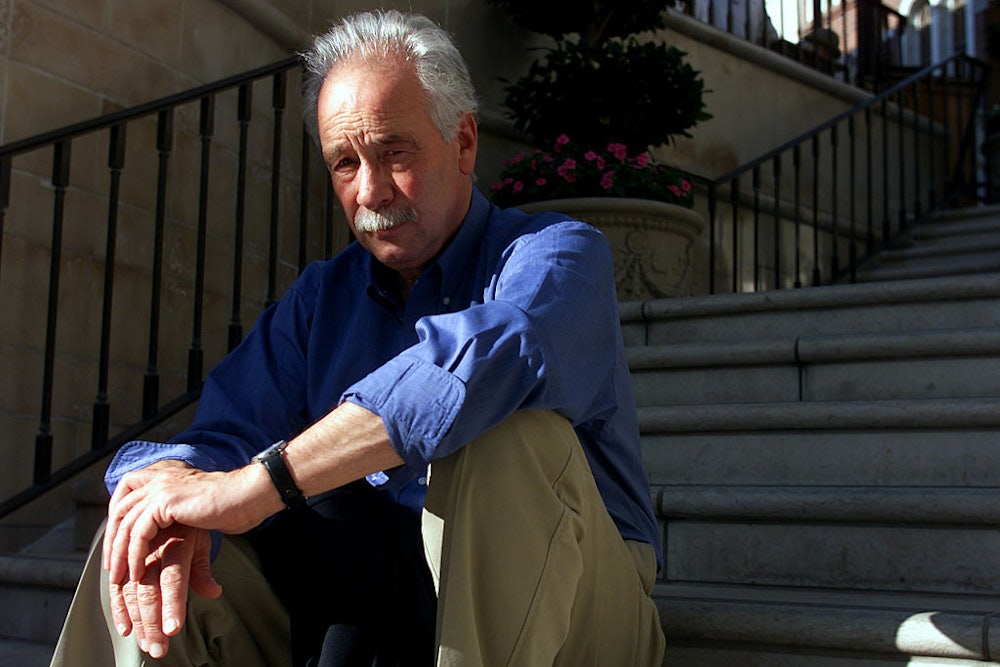
Gina Ferazzi/Los Angeles Times/Getty Images
W.G. Sebald 将异化视为一种行动主义形式。
W.G. Sebald 于 2001 年 12 月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 57 岁,当时他的小说 Austerlitz 出版几个月后,他的文学声誉达到了顶峰。他的去世让读者们意犹未尽。从那以后,他的出版商不断深入挖掘他的作品,以推出遗作。自他去世以来,已经有六本完整的书以英文出版,现在,在他去世 23 年后,我们迎来了第七本——也许也是最后一本:《Silent Catastrophes: Essays》。
乍一看,这本书可能会让普通读者感到望而却步:它的基调偏学术化,专注于美国经常忽视的文学传统,其中许多作家在英语国家鲜为人知。但它专注于奥地利——一个衰落的帝国,为了重拾昔日的辉煌,缓慢但自愿地沦为法西斯主义——这意味着《Silent Catastrophes》不幸地诞生于一个恰当的时机。愿意深入研究学术风格的读者很快就会发现,不仅 Sebald 的标志性关注点浮出水面,而且还会发现关于我们如何应对帝国衰落和权威主义兴起的意外思考。
通过对影响他的作家的解读,这些早期的作品清楚地表明了指导 Sebald 伟大作品的伦理原则:忧郁远非失败主义,它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抵抗,一种通过保存过去来对抗抹去法西斯主义阴谋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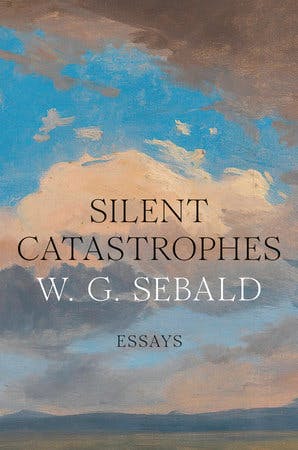 Silent Catastrophes: Essays
by W.G. Sebald
Buy on Bookshop
Random House, 544 pp., $30.00
Silent Catastrophes: Essays
by W.G. Sebald
Buy on Bookshop
Random House, 544 pp., $30.00
进入《Silent Catastrophes》的最初障碍是它的文风:由一位在 1980 年代还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学者所写,它带有许多不适合休闲阅读的风格特征。书中对读者缺乏友好的引导——例如,它假定你已经了解他所讨论的作家——但充其量,只有少数(Thomas Bernhard、Franz Kafka、Peter Handke、Elias Canetti 和 Arthur Schnitzler,他的《Traumnovelle》被 Stanley Kubrick 改编成《Eyes Wide Shut》)会被大多数非专业的英语读者所熟悉。这本书是两本独立的评论著作的汇编——《The Description of Misfortune》(1985)和《Strange Homeland》(1991)——给人的感觉就像你已经了解了围绕这些作家的评论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有时感觉就像你已经漫步到一个完全为其他奥地利文学专家准备的大学小组讨论中。
与其将《Silent Catastrophes》视为一系列学术论文,我发现将这本书读作一幅描绘危机中的国家和帝国的群体肖像更有价值,其作家既叙述了衰落,又试图以各种方式和不同程度的成功来抓住某种意义。我开始对这些作家的细微之处不太感兴趣,而更感兴趣的是了解奥地利的衰落——通过其作家折射出来——告诉我们今天什么。
Sebald 于 1944 年出生于德国乡村,但他的成年生活大部分时间都在英国诺维奇度过,他写这些书时是一位生活在撒切尔时代的英国的移民;很难不感受到那些灾难性的岁月在本书背景中的回响。正如编辑和长期 Sebald 学者 Jo Catling 在她的介绍中所阐述的那样,《Silent Catastrophes》中的文章追溯了那些将奥地利作为家园变得 unheimlich 的作家的作品:“不仅仅是‘不舒适’,而且既充满敌意又令人不安,在两种意义上都很奇怪。” 对于那些可能在 2025 年感到自己的家园变得充满敌意和令人不安的人来说,这里有很多东西可以帮助理解这种怪异的感觉,并且一再尝试规划某种前进的道路。
一种简单的方法是关注那些在美国已经广为人知的作品,包括 Franz Kafka 的《The Castle》和 Elias Canetti 的《Crowds and Power》,Sebald 在这里对这两部作品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在两部作品中,一部写于第三帝国之前,另一部写于第三帝国之后,Sebald 追踪了权威权力运作方式的相似线索:权威权力源于对混乱和无序的仇恨,试图通过暴力来控制这片土地,以寻求强制执行一种死板的秩序。正如他在对 Canetti 作品的评论中所指出的那样,“渴望完全秩序不需要生命。” 事实上,这种对秩序的渴望“是一种杀人的渴望。帝国作为一片沙漠,住所作为一座陵墓,秩序的创造者可以在其中以自己选择的姿势和绝对安全地永恒休息——事实证明,这些是偏执狂想象力所渴望的最终模型。” 这种暴力病态地仇恨差异、陌生感和混乱,推崇埃及金字塔和陵墓、毫无血色的罗马柱以及 Albert Speer 为他的元首 conjured 出来的无菌混凝土巨型结构。
Sebald 注意到,Kafka 从根本上认识到权力是“寄生的而不是强大的”。
正如 Sebald 在 Kafka 的《The Castle》中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权力“绝不是创造性的;它是完全无菌的,其唯一目的似乎是毫无意义的自我延续。” Kafka 作品中的暴君无休止地榨取被压迫者的生命,除了他们自己吸血鬼般的需求,即不断以生命为食之外,根本没有明确的理由来实施这种暴力。 Sebald 注意到,Kafka 从根本上认识到权力是“寄生的而不是强大的”。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停止询问亿万富翁 想要什么,因为现在他们除了权力本身之外什么都不想要;尽管他们采取了所有的行动和暴力,但他们自相矛盾地失去了所有的能动性,除了仅仅为了积累 更多 而存在之外,无法做任何其他事情。
但仅仅认识到权威主义者是如何运作的已经不够了,如果《Silent Catastrophes》仅仅是诊断性的,那将是一回事。Sebald 在他去世几十年后仍然引人入胜的原因在于他标出了可能的抵抗路线——不是以传统意义上的抗议、见证和行动主义(所有这些,不用说,仍然至关重要和必要)而是通过完全不同的方式。
贯穿他所有作品的一个关键观察结果,并且在这里进行了明确的讨论,是法西斯主义如何使我们与自然世界(混乱和无序)疏远,并且在权威主义心态中,自然的“救赎”“只能通过暴力来实现”,因为只有通过暴力“混乱才能变成秩序;而这种转换使使用暴力合法化,将其视为一种准神圣的创造行为。” (Donald Trump 命令 淹没北加州,这是一场巨大的水资源浪费,毫无作为,只是最新的一次迭代。Trump 与自然疏远并鄙视它,他认为它只不过是他自己力量的反映:他希望看到水从水坝中涌出,因为它反映了他自己扭曲让他感到恐惧和困惑的景观的能力。)
因此,我们对周围自然世界的关注,不仅必须包括对气候变化的关注以及我们减轻气候变化的需求,还必须包括对自然的新敬畏之情,将自然视为混乱和未成形的,复杂到超出我们的范围。 尝试参与自然世界,无论以何种形式,都不仅仅是逃避现实;这是一种尝试——如果不是为了与自然重新建立联系——至少要记录我们与自然之间爆发的裂痕,这种裂痕每天都在稳步扩大。
对于 Sebald 来说,我们与这个自然世界的疏远,受到权威主义和现代灾难的加速和加剧,采取了一种忧郁的形式,这是他所有作品中的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 但是,这种忧郁不必被理解为某种颓废的退缩或宿命论。 正如 Sebald 在他对 Hermann Broch 的讨论中所说的那样,“在美学领域,就像在遗传学或机器理论领域一样,重言式的逻辑功能在于它 不 包含任何信息;它在伦理层面的对应物是失败主义。” Sebald 并没有将忧郁视为放弃和失败,或者仅仅是临床抑郁症的另一个同义词,而是在寻找一种忧郁的政治——一种将这种对普遍灾难的反应转化为一种行动主义本身的方式。
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 首先,它涉及重新呼吁教学,Sebald 认为,教学在奥地利文学传统中一直非常重要(“与德意志帝国形成对比”)。 或许,我们已经变得过于习惯于从有限的目的地来思考学习:获得学位、掌握特定技能等等。 随着知识现在日益受到攻击,我们可能需要建立替代的教学和学习网络——在大学和证书之外; 扩散的教师和学习者网络,可以更具弹性和主动性。
同样重要的是,在强调这些奥地利小说家时,Sebald 在这里呼吁一种抵制变得完整、完美、理想的欲望的艺术——因为他认为,其中蕴含着与法西斯主义相似的冲动。 “艺术的不变性表明它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就像权力系统一样,将其自身熵的恐惧投射到想象中的肯定或破坏性结局上,”他评论道,并补充说“已经在伟大的交响乐中,在最后的音符中听到了破坏的欲望。”
正是在这种冲动中,Sebald 自己的伟大作品的奇怪不完整性才得以凸显:他的最后一部小说《Austerlitz》以或多或少地草草结尾的方式,以及他早期的作品通过拼贴和组合而不是统一和连贯的设计来形成的方式。 它还有助于理解他标志性的照片和其他图像的使用,这些照片和其他图像打破并中断了他的文本,这样做不是作为一种说明形式,而是作为一种刺耳的声音形式。 与“伟大的艺术”“总是面向永恒价值”相反,我们将继续需要更多“由剩余物和碎片组成的修补匠的作品”,这些作品“已经蕴含了即将到来的破坏”。
最关键的是 Sebald 在《The Description of Misfortune》的介绍中提出的尝试,即提供另一种思考忧郁的方式——不是作为抑郁,而是作为实践。 “忧郁,对正在发生的灾难的沉思,”他写道,“与对死亡的渴望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这是一种抵抗形式。” 对于 Sebald 来说,忧郁是一种保存力量,一种保持过去活力的手段——也许是破碎和废墟,但仍然处于意识的最前沿。 “特别是在艺术层面上,它的功能绝不是被动的或反动的,”因为在保持过去固有的可能性活着的同时,人们也保留了对未来的希望。
或许,这样的未来是我们目前无法实现的,但忧郁者仍然紧紧抓住这一点,就像一位知道他们的知识和资源必须随时准备被召唤的档案管理员一样。 “当忧郁以固定的目光再次考虑事情是如何变成这样的时,很明显,绝望的机制与驱动我们知识和洞察力的机制相同。 对不幸的描述包含了克服它的可能性。” 对于 Freud 来说,哀悼是正常的,是一个健康的处理损失的过程,而忧郁是病态的,是一种无法继续前进的状态——Sebald 完全颠倒了这一点,暗示不仅忧郁不是病态的,而且恰恰是在拒绝继续前进中才能找到政治抵抗。
Sebald 的大部分作品都根植于这样一种意识,即尽管记忆和历史是反复无常的、经常是矛盾的并且不可能永久固定,但记录和保存所有这些,甚至是矛盾和混乱,仍然至关重要。 因为艺术家的工作——即使他们可能是忧郁的——是在这些矛盾的过去中筛选,以寻找可能仍然对我们开放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