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迷雾:对 Operation Babylift 的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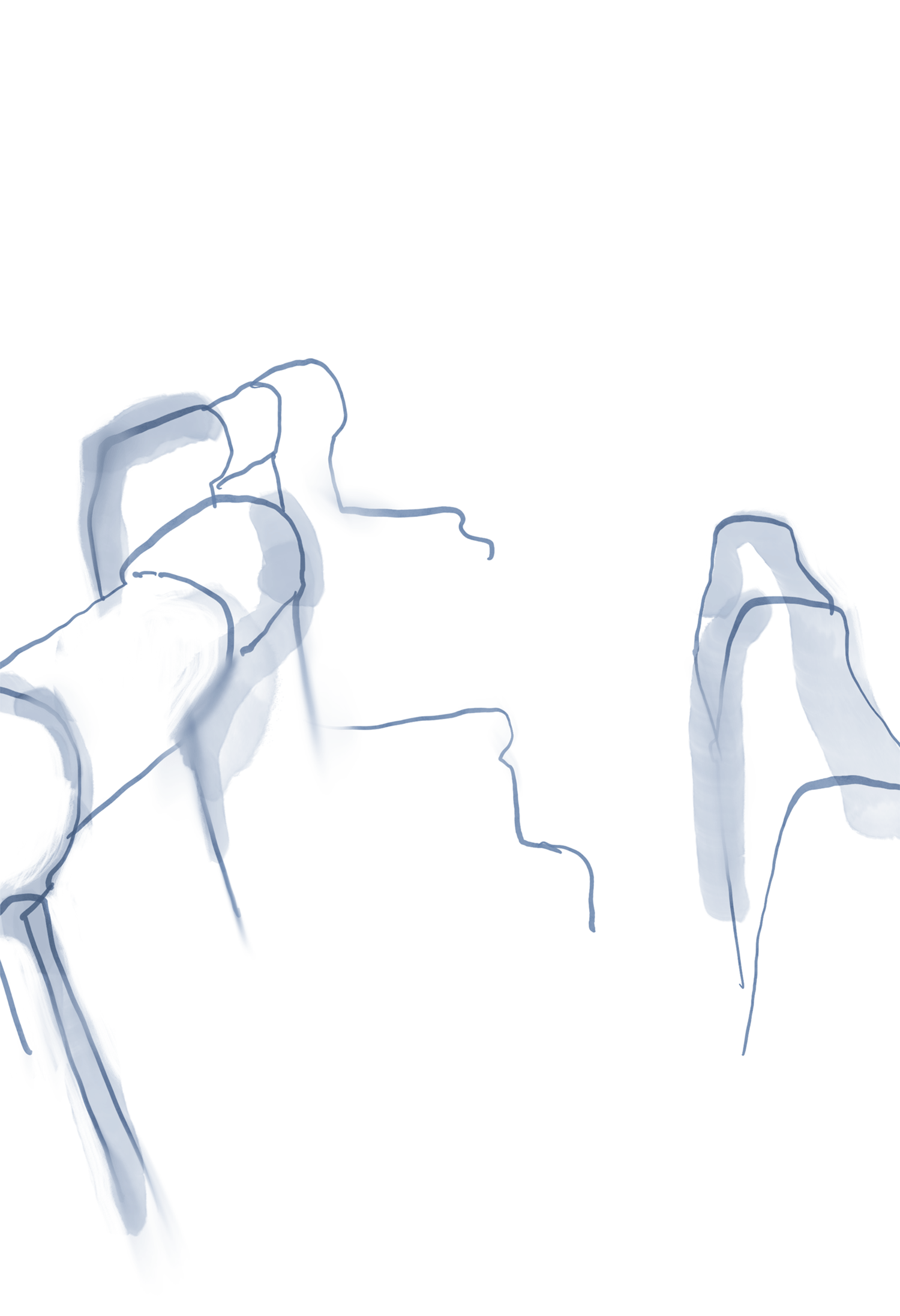

Out of the Fog
作者: Camille.Bromley 日期: 2025年4月21日 插画: Nguyen Tran
Operation Babylift 是在西贡沦陷期间,为拯救儿童而做出的真诚尝试。几十年后,一代被收养者正在与这场行动的后果作斗争。
在 1975 年,听美国人说来,大规模收养越南儿童是一个关于拯救和救赎的故事。这些孩子是战争婴儿,bụi đời,尘埃之子。十年的死亡,加上美国军事基地附近蓬勃发展的性交易,使得近 20,000 名儿童进入了整个南越的 100 多个孤儿院。到了四月,随着越共席卷海岸,据说混血儿童正处于危险之中。传言说,北方军队会找到外国后裔,并从他们的身体上挖出肝脏来吃。出于恐惧和绝望,母亲们放弃了自己的婴儿——许多婴儿体重不足、生病或被战争致残——交给美国人。然后美国人把他们带走了。
越南收养的流行叙事是这样开始的:
 在西贡的一所学校里,孤儿们在 1975 年 4 月的 Operation Babylift 期间,在前往美国之前得到照顾和集中。
照片由 Jean-Claude Francolon/Gamma-Rapho 通过 Getty Images 提供
在西贡的一所学校里,孤儿们在 1975 年 4 月的 Operation Babylift 期间,在前往美国之前得到照顾和集中。
照片由 Jean-Claude Francolon/Gamma-Rapho 通过 Getty Images 提供
 在西贡的一所学校里,孤儿们在 1975 年 4 月的 Operation Babylift 期间,在前往美国之前得到照顾和集中。
照片由 Jean-Claude Francolon/Gamma-Rapho 通过 Getty Images 提供
在西贡的一所学校里,孤儿们在 1975 年 4 月的 Operation Babylift 期间,在前往美国之前得到照顾和集中。
照片由 Jean-Claude Francolon/Gamma-Rapho 通过 Getty Images 提供
并这样结束:
 Edna Deichl(左),Free Flight 飞行员的妻子,小睡片刻,而 Linda Reid(中),副驾驶的妻子,以及 Lillian Bradshaw(右),一位孤儿院工作人员,在从西雅图飞往芝加哥的航班上喂养她们照顾的孩子,将越南儿童带到他们的新家。
照片由 Barry Sweet/Associated Press 提供
Edna Deichl(左),Free Flight 飞行员的妻子,小睡片刻,而 Linda Reid(中),副驾驶的妻子,以及 Lillian Bradshaw(右),一位孤儿院工作人员,在从西雅图飞往芝加哥的航班上喂养她们照顾的孩子,将越南儿童带到他们的新家。
照片由 Barry Sweet/Associated Press 提供
 1975 年 4 月 5 日 – 飞机内部 – 旧金山国际机场 – 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 – Gerald R. Ford、医务人员、护士、难民儿童、其他人在交谈,抱着孩子 – 来自南越的 Operation Babylift 飞机的抵达
由 Gerald R. Ford 总统图书馆提供
1975 年 4 月 5 日 – 飞机内部 – 旧金山国际机场 – 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 – Gerald R. Ford、医务人员、护士、难民儿童、其他人在交谈,抱着孩子 – 来自南越的 Operation Babylift 飞机的抵达
由 Gerald R. Ford 总统图书馆提供
救援人员称之为“抢救行动”。 护士 Cherie Clark 回忆说,“我们实际上是在捡起婴儿,并试图让他们活得足够长,以便将他们安置领养。” Clark 最终通过她的收养组织 Friends of Children of Vietnam (FCVN) 从越南送走了大约 1,200 名儿童。
随着美国明确将完全撤出在越南的驻军,总统 Gerald Ford 在 4 月初宣布了 Operation Babylift。 Ford 将 Babylift 描述为一项人道主义“慈悲任务”。 同样重要的是,它也是对军事失败和抛弃的一种转移。 一个月后,2,894 名越南和柬埔寨儿童正在前往美国家庭的路上; 大约 1,300 名其他儿童被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整个欧洲收养。
一些第一批儿童被空运到一架 C-5A Galaxy 运输机上,这架飞机的内部空间可以与体育馆相媲美。 孤儿院工作人员将 200 多个孩子装入货舱,正如记者 Dana Sachs 在她的书 The Life We Were Given 中所描述的那样,这是一项“就像试图在皮卡车的车厢里携带松散的鸡蛋”的努力。 起飞十二分钟后,飞机后部的一扇门被炸开,在飞机侧面撕开了一个洞。 飞机坠入稻田,压碎了儿童所在的货舱——138 人死亡,其中包括 78 名婴儿。
 1975 年 4 月 5 日的《纽约每日新闻》封面。 (标题中的死亡人数与后来确认的 138 人死亡人数不符。)
1975 年 4 月 5 日的《纽约每日新闻》封面。 (标题中的死亡人数与后来确认的 138 人死亡人数不符。)
 救援和恢复人员搜寻一架载有越南孤儿的 C-59 Galaxy 飞机的残骸。 该飞机在 Operation Babylift 的首次飞行中,从西贡的 Tan Son Nhut 机场起飞后不久坠毁。 78 名儿童和大约 50 名成年人死亡; 大约 170 人幸存。 随后的航班疏散了 2,5000 多名儿童到美国和其他国家进行收养。
照片由 Sal Veder / AP Photo 提供
救援和恢复人员搜寻一架载有越南孤儿的 C-59 Galaxy 飞机的残骸。 该飞机在 Operation Babylift 的首次飞行中,从西贡的 Tan Son Nhut 机场起飞后不久坠毁。 78 名儿童和大约 50 名成年人死亡; 大约 170 人幸存。 随后的航班疏散了 2,5000 多名儿童到美国和其他国家进行收养。
照片由 Sal Veder / AP Photo 提供
Operation Babylift 继续进行,没有喘息的机会。 第二天,324 名儿童,包括前一天坠机事件的幸存者,被装上了一架商业泛美航空公司的航班。 这次,穿着白色睡衣的婴儿被整齐地包装在纸板箱中。 装有婴儿的盒子像随身行李一样楔在座位下。 有些婴儿被系在红色和黄色的飞机座位上,像小玩偶一样垂头丧气。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越南的七个美国和国际收养组织竞相确保飞机上有空间容纳他们照顾的儿童。
一位南越中尉向《纽约时报》发表了以下痛苦的声明:“很高兴看到你们美国人在离开时把我们国家的纪念品带回家——瓷象和孤儿。 可惜他们中的一些人坏了……但我们还有很多。”
美国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从国外收养了儿童,最著名的是从韩国收养,但 Operation Babylift 围绕收养创造了一个故事,将外国婴儿的流离失所转变为美国人的家庭成为一种慈善行为。 在战争的恐怖中,出现了一个行善和赦免的机会。 “每个人都在战争中受苦,但没有人比儿童更受苦,空运是我们至少可以做的事情,”Ford 在他的自传中写道。 这种叙事并非没有受到批评——Grace Paley 在 Babylift 时期为《Ms. Magazine》撰稿,称其为“愤世嫉俗的政治游戏”——但即使那些承认该运动后勤令人震惊的混乱的人也认为收养本身是双赢的。 马萨诸塞州的一位参议员这样说:“简单地说,在美国的精英主义中生活比在越南死去要好。”
 Operation Babylift 航班上的婴儿。
照片由 Jean-Claude FRANCOLON/Gamma-Rapho 通过 Getty Images 提供
Operation Babylift 航班上的婴儿。
照片由 Jean-Claude FRANCOLON/Gamma-Rapho 通过 Getty Images 提供
 52 名越南儿童乘坐 World Airways 飞机抵达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机场。
照片由 Jerry Telfer/《旧金山纪事报》通过 Getty Images 提供
52 名越南儿童乘坐 World Airways 飞机抵达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机场。
照片由 Jerry Telfer/《旧金山纪事报》通过 Getty Images 提供
 旧金山国际机场救护车内部,医务人员抵达来自南越的 Operation Babylift 飞机。 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 1975 年 4 月 5 日。
由 Gerald R. Ford 总统图书馆提供
旧金山国际机场救护车内部,医务人员抵达来自南越的 Operation Babylift 飞机。 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 1975 年 4 月 5 日。
由 Gerald R. Ford 总统图书馆提供
 1975 年 4 月 11 日:新生活从这里开始,旧金山 Presidio 的 Harmon Hall 挤满了床垫、志愿者和 Operation Babylift 中的越南孤儿。 从南越空运到美国的孤儿住在床垫上四天,因为他们正在为未来的收养进行处理。
照片由《丹佛邮报》通过 Getty Images 提供
1975 年 4 月 11 日:新生活从这里开始,旧金山 Presidio 的 Harmon Hall 挤满了床垫、志愿者和 Operation Babylift 中的越南孤儿。 从南越空运到美国的孤儿住在床垫上四天,因为他们正在为未来的收养进行处理。
照片由《丹佛邮报》通过 Getty Images 提供
当第一批 Babylift 飞机开始降落在旧金山时,很快就清楚的是,许多儿童实际上并不是孤儿。 住在附近的越南妇女 Nhu Miller 来到 Presidio 为年龄较大的儿童翻译,发现有些人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他们想见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 “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他们问。 在混乱中,许多人缺乏身份证明文件; 他们的文件丢失、混淆或伪造了。 Miller 后来表示,“我帮助他们,看到人们只是像挑选小狗一样挑选他们。”
人们如何看待 Babylift——作为一项拯救儿童的任务还是绑架他们——部分取决于人们如何定义收养的目的。 是为了 提供 一个孩子,还是为了 向 热切的西方父母 提供一个孩子? FCVN 和其他收养机构,以及准父母,不顾一些儿童有其他选择的证据,坚持进行他们的收养。 他们认为一个充满爱的家庭具有恢复能力。 一位 Operation Babylift 儿童的养父母说:“让我们忘记政治,想想孩子们。” 这种态度在今天仍然盛行。
这些孩子的生母很少被考虑。 然而,有些人拒绝被遗忘。 一位母亲 Anh Thi Hoang Doan 在将她的七个孩子托付给 FCVN 四个月后,作为难民抵达南加州的 Camp Pendleton,她相信该机构会将她的孩子安全地运送到美国。 她计划加入他们。 她向该机构解释了这些条件,并且——不打算放弃她的孩子——她没有签署收养协议。 一旦到了加利福尼亚,Doan 很快就找到了她的几个孩子。 第五个孩子 Binh 被爱荷华州的一对夫妇收养。 这对夫妇拒绝归还这个男孩。 Doan 起诉要求获得监护权,这对夫妇提出了上诉。 最终,在 18 个月后,她赢回了 Binh。 她的最后一个孩子 Than 在 FCVN 的洗牌中迷失了。 Doan 于 2021 年去世,从未找到他。
 “我的脸是什么? 我的人民是谁? 我来自哪里?”
“我的脸是什么? 我的人民是谁? 我来自哪里?”
Operation Babylift 的任务随着越南婴儿抵达他们在美国家庭而结束。 对于人道主义者和新父母来说,这构成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但是,随着孩子们长大,他们的故事继续走向其他结局。
“我的收养不是那些幸福美好的故事之一,” Lynelle Long 告诉我。 她于 1973 年从越南带到澳大利亚,当时她五个月大。 她直到十几岁才被正式收养。 “我遭受了多年的虐待,”她说。 Long 去年向澳大利亚移民部长作证,她在其中谈到了遭受几个家庭成员的性虐待。 两年前,她的养父承认了虐待行为,Long 在法律上取消了她的收养。 在她的护照中,“出生地”一直被列为澳大利亚。 她终于将其更改为真实的地点:越南。
在越南战争之前,澳大利亚没有收养的历史,因此 Long 是第一批抵达该国的儿童之一。 当时,没有人谈论收养。 “我只是在成长过程中感到奇怪、怪异、孤立、非常孤独,”她告诉我。 当 Long 二十岁出头时,她开始寻找像匿名戒酒会这样的会议,专门为来自国外的被收养者举办。 但没有。 她加入了一个国内被收养者的团体,但当她参加时,她发现他们没有谈论与他们的白人家庭长相不同的经历,也没有谈论每天面临的种族主义暗流。 她问小组组织者是否曾经收到过其他像她这样的被收养者。 他们告诉她,偶尔会有一些人过来。 她给了他们她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并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这样做就分享它。 几年后,当时在 IBM 工作的 Long 将这些偶然的联系变成了一个在线小组,面向世界各地被外国收养的任何人。
InterCountry Adoptee Voices 成了被收养者寻找法律咨询、心理健康问题帮助以及有关如何找到其生身家庭的信息的生命线——所有这些在 Babylift 之后的几年里都没有得到政府的提供。 美国不为国际收养儿童提供福利金检查,使他们面临潜在的伤害。 2022 年,对大约 800 名韩国被收养者的研究发现,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受到养父母的虐待。 美国政府也没有收集有关被收养儿童后来生活中的福祉的信息。 然而,跨国被收养的青少年比未被收养的儿童更容易患上严重的精神健康障碍。 “作为一个被带走的孩子,我从来没有能力保护自己。 我没有发言权,”Long 在她的证词中说。
 第一架 Operation Babylift 航班上的儿童。
照片由 AP Photo/File 提供
第一架 Operation Babylift 航班上的儿童。
照片由 AP Photo/File 提供
 Operation Babylift 航班上的婴儿。
由 Gerald R. Ford 总统图书馆提供
Operation Babylift 航班上的婴儿。
由 Gerald R. Ford 总统图书馆提供
 花花公子兔子帮助将婴儿从纽约 LaGuardia 机场的一架飞机上抱下来。 这架喷气式飞机是花花公子出版商 Hugh Hefner 特别包租的。
照片由 Bettmann Archive / Getty Images 提供
花花公子兔子帮助将婴儿从纽约 LaGuardia 机场的一架飞机上抱下来。 这架喷气式飞机是花花公子出版商 Hugh Hefner 特别包租的。
照片由 Bettmann Archive / Getty Images 提供
并非每个收养故事都如此令人清醒,但即使是那些被安置在幸福家庭中的孩子,也会对自己的历史产生复杂的情感。 2000 年,一位名叫 Indigo Willing 的社会学学生创办了第一批越南被收养者团体之一,名为 Adopted Vietnamese International (AVI)。 Willing 于 1972 年从越南被收养到悉尼郊区。 她告诉我,她的家人很爱她,但这并没有让她忘记她是如何到达那里的。 她将被收养者比作在地球上漫游、寻找答案的迷失的灵魂。
“没有哪一天我不照镜子,我想知道,‘我的脸是什么? 我的人民是谁? 我来自哪里?’” 她告诉我。 AVI 现在是一个拥有大约 2,000 名成员的 Facebook 群组,人们在其中分享婴儿照片和政府飞行名单的扫描件。 他们列出他们的生母的名字和 50 年前的地址,并问:“如果你知道任何事情,请告诉我。” 他们为返回越南分发 DNA 试剂盒筹款,希望扩大生身家庭的数据库。 他们组织文化遗产之旅。 Willing 曾前往越南,但她从未找到她的生父母。
我与之交谈的许多被收养者都形容自己从根本上是不完整的。 他们生活中缺席的部分与存在的部分一样重要。 “我的叙述是我身份的来源,但也提醒我,我不是什么,也没有什么。 我介于一个完整的故事和一个永远无法完全了解的故事之间,” Bert Ballard 在一个 收养故事选集 中写道,他三周大时从西贡的 An Lac 孤儿院被空运出来。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一些被收养者在其他被收养者中找到了最亲密的家庭感。 在 Facebook 群组中,被收养者有时会互相称呼为兄弟姐妹。 “你们是我的家园,”一位韩国被收养者在 2018 年的一次会议上对一屋子的其他被收养者说。
Jane Joy 于 1973 年从西贡被收养,并在纽约州西部的白人家庭中长大。 几年前,她创建了一个名为 Vietnamese Adoptees 的 Facebook 群组,她将其限制为仅限被收养者。 她告诉我,养父母的善意和受伤的感觉往往会限制他们收养的孩子被允许谈论的内容。 “我记得我七八岁的时候,感觉不长得像我的家人身体上会很痛。 我记得我对我的妈妈说,‘我只是希望我有金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 她不明白,”Joy 告诉我。 “对她来说,我的观点没有道理。 哦,但你与众不同。 我不想与众不同。 那是我最不想要的。”
 机组人员协助越南儿童登上飞往菲律宾的 Operation Babylift 航班。
由 Gerald R. Ford 总统图书馆提供
机组人员协助越南儿童登上飞往菲律宾的 Operation Babylift 航班。
由 Gerald R. Ford 总统图书馆提供
 在菲律宾的空军人员与越南儿童。
由 Gerald R. Ford 总统图书馆提供
在菲律宾的空军人员与越南儿童。
由 Gerald R. Ford 总统图书馆提供
Long、Willing 和 Joy 属于通常所说的第一代越南被收养者,他们现在 50 多岁和 60 多岁。 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里,最广泛流传的 Babylift 的第一人称叙述是由 Cherie Clark 等人道主义工作者撰写的回忆录,而为纪念 Babylift 而举行的活动是由收养机构和航空公司举办的。 但是,随着第一代被收养者成年,他们开始表达自己的观点。 在黑暗中摸索着找到彼此之后,被收养者为他们的经历形成了一种共同的语言。 他们谈论“走出迷雾”——学会质疑他们的生父母经常传递下来的白人救世主叙事。 他们出版了回忆录,制作了纪录片和电影。 许多人设法找到并与他们的生身家庭团聚。 他们创造了一种收养的反叙事,承认了他们故事中的悲伤、失落和愤怒的现实。
记者 Erika Hayasaki 的最新著作 Somewhere Sisters 讲述了一个收养的非凡完整故事,从出生到搬迁,再到团聚及其后果。 1998 年在 Nha Trang,一位名叫 Liên 的 26 岁越南妇女早产了一对双胞胎女儿。 两人都生病了,体重不到四磅。 Liên 没有工作,也没有家,父亲也不见了。 她将双胞胎带到附近的一家孤儿院,该孤儿院接受了一个名叫 Loan 的女孩。 Liên 的另一个女儿 Hà,她委托给她的妹妹照顾。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Liên 断断续续地探望她的女儿们。 有一天,她来到孤儿院,被告知 Loan 已被一个美国家庭收养。 她没有被告知他们的名字,但我们得知他们是 Solimenes,一个富裕的家庭,住在一个芝加哥郊区的大房子里。 这次收养是由母亲 Keely 推动的,她在 9/11 事件后,想为世界做一些好事和有意义的事情。
与此同时,Hà 在她的村庄里过着贫穷但快乐的童年。 13 岁时,Loan 经过 Keely 多年的努力,终于与她的妹妹 Hà 和母亲 Liên 团聚。 她坚持寻找 Hà 和 Liên——获得翻译人员、追踪线索以及亲自多次访问 Nha Trang——是一种慷慨的行为,但它也清楚地表明了收养家庭对团聚的完全控制。 Keely 让它发生,但只是根据她的动机和她的时间安排。 早期,Liên 给 Keely 写了一封信,告诉她她渴望与 Loan 重新建立联系。 但 Keely 还不能准备好再等六年。 她没有回复。
 在黑暗中摸索着找到彼此之后,被收养者为他们的经历形成了一种共同的语言。
在黑暗中摸索着找到彼此之后,被收养者为他们的经历形成了一种共同的语言。
美国吸收的被收养儿童比其他所有国家加起来还要多。 2004 年,在国际收养的顶峰时期,美国家庭收养了近 23,000 名儿童。 从那以后,国际收养到美国的数量减少了 90% 以上,这主要是由于旨在消除贩运的海牙公约条例。 在其他国家,围绕收养的叙事已经变味。 当一名 10 岁女孩遭受虐待和死亡促使该国禁止所有国际收养时,埃塞俄比亚每年向美国输送数千名儿童。 今天,该国的官方政策是每个埃塞俄比亚儿童都应该在埃塞俄比亚长大。 中国——累计向美国输送儿童最多的国家——去年停止了海外收养。 当国际收养确实发生时,海牙公约指南建议该过程应受到监管,并且应保留生身家庭的联系信息,并在孩子需要时提供。
目前,西方国家有超过一百万人被外国收养,其中包括美国以亚裔美国人为主的成年被收养者人口。 这是一个在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群。 第一代已经找到了他们的声音; 最年轻的群体现在正成年。 他们也处于独特的地位,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珍视的家庭制度是如何为政治目的而提供或扣留的。
今天一些美国被收养者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是,令人震惊的是,被剥夺公民身份。 直到 2001 年,美国的外国收养都通过与国内收养相同的法律途径进行。 结果是,使外国出生的儿童归化并没有发生在该过程的一部分。 父母必须单独为孩子的公民身份提出申请,并且他们中的许多人要么从未被告知,要么从未这样做。
 总统 Gerald Ford 抱着一个越南婴儿,这个婴儿乘坐 Operation Babylift 航班之一抵达旧金山。
由 Gerald R. Ford 总统图书馆提供
总统 Gerald Ford 抱着一个越南婴儿,这个婴儿乘坐 Operation Babylift 航班之一抵达旧金山。
由 Gerald R. Ford 总统图书馆提供
Kris Larsen 的父母在他被从 Operation Babylift 航班在关岛收养后,确实为他申请了美国公民身份。 他们认为他收到了,因为他们没有听到其他消息。 但是他的文书工作从未得到处理。 2012 年,Larsen 四十岁出头,正在西雅图服刑,当时 ICE 检查标记了他。 他不是美国公民的消息让他感到莫名其妙。 “我有点不当回事,因为我就像,‘那是不可能的。 我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 他告诉我。 他的家人告诉他这是一个错误,不用担心。 在他获释时,当他的家人去监狱见他时,ICE 反而接走了他。 他在他们的驱逐名单上。
2000 年,国会通过立法,向所有 18 岁以下的被收养儿童授予公民身份。 但该法律不适用于被收养的成年人,包括 Operation Babylift 的成员和来自韩国、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数千名其他被收养者。
与 Larsen 交谈时,我犯了一个错误,称他的情况为“无证”。 他很快纠正了我。 他从未无证。 2022 年,他申请了赦免,他收到了赦免,并重新获得了绿卡。 现在,在他 50 多岁的时候,他正在申请公民身份。
大约 10 年前,在几名韩国被收养者被广泛宣传的驱逐出境之后,其中一人自杀,一项运动开始游说立法,该立法将向 2000 年法律中遗漏的被收养者授予公民身份——一个潜在人数达数千人的群体。 拟议的法案《被收养者公民身份法》尚未通过。 保守派反对者将其归类为不受欢迎的“移民法案”,并要求将有犯罪记录的被收养者和已经驱逐出境的数十名被收养者排除在该法案之外。
 52 名越南儿童乘坐 World Airways 飞机抵达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机场。
照片由 Jerry Telfer/《旧金山纪事报》通过 Getty Images 提供
52 名越南儿童乘坐 World Airways 飞机抵达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机场。
照片由 Jerry Telfer/《旧金山纪事报》通过 Getty Images 提供
 Operation Babylift 航班上的婴儿。
照片由 Peter O’Loughlin/AP Photo 提供
Operation Babylift 航班上的婴儿。
照片由 Peter O’Loughlin/AP Photo 提供
Monte Haines 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于 2009 年被驱逐到韩国。 五名 ICE 特工护送他下飞机,在他的口袋里放了 20 美元,然后离开了。 那是十一月。 Haines 穿着一件 T 恤和短裤。 他没有行李、没有电话、没有身份证。 他不会说韩语。 三周以来,他睡在一座桥下,从垃圾堆里捡东西吃。 “就像乒乓球一样,” 他在几年前的 一个小组讨论中说。 “首先是韩国政府把我送到美国,然后从美国他们又把我送回韩国。”
Operation Babylift 的孩子,以及美国战争的所有其他后裔,既是被收养者,也是难民。 但他们不是自愿移民,也不是外国人。 拒绝向像 Larsen 和 Haines 这样的美国被收养者提供公民身份表明,美国家庭的仁慈拥抱始终是有条件的,以牺牲更脆弱的家庭甚至儿童为代价。 在美国,收养从未消除孩子的外国性。 那些长大后被指控犯罪的人最脆弱,突然被标记为不配属于。 这种逻辑在 Donald Trump 总统的领导下以更加阴险的形式延续,他抛弃了任何拯救儿童的观念,而是直截了当地威胁他们。 他在 2018 年的家庭分离政策将大约 5,500 名移民儿童与他们的家人分离,以广播政治警告; 仍有一千多人未团聚。 他今年早些时候采取的取消出生公民权的举动是赤裸裸地企图剥夺美国的非白人儿童对美国家庭的主张。
Long 从未找到她的生身家庭。 尽管如此,她觉得她的故事是完整的。 “即使没有找到你的生身家庭,你也可以找到平静。 这不是必要的。 找到你自己的过程是必要的,” 她说。 与此同时,Haines 设法搬进了一间单间公寓,并在一家披萨店找到了一份工作,但他从未找到家。 他在首尔的新同胞看着他,就像他是个外国人一样。 “我和你一样,都是韩国人,” 他告诉他们。 他没有返回美国。
-
Cookie Settings
© 2025 Vox Media,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Don't miss the big ones. Subscribe for full access to our reviews, scoops, and analysis. SUBSCRIBE NOW